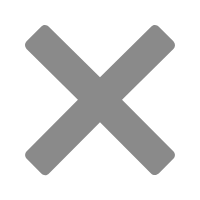-
临渊念池鱼
1
庶妹为了顶替我嫁给博贤王府的小公爷,造谣我与马夫有染。
父亲宠妾灭妻,任凭姨娘将我当街折辱后嫁给马夫做妾。
十年后,庶妹被王爷厌弃扔到郊外。
而马夫却因救驾有功,钱权双收,连我也受赏封了郡主。
庶妹发疯杀了我,和我一同重生在长街受辱当日。
1
一个用尽全力的巴掌落在我脸上。
“嫡女又如何?还不是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腌臜事来!”
刚睁开眼,庶妹就带着几个仆从强行将我按在地上。
不等我分辩,就把一团臭抹布塞进我的嘴巴。
池琬贴近我的耳边,恶狠狠道:
“你一个嫁给马夫还不安分的贱人,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也能当上郡主。”
“既然上天给我一回重来的机会,这次,你哪里都不要肖想了。”
原来她也重生了。
我被五花大绑着拴在马屁股后面。
马夫一言不发地跪在地上,见我被拽过来,双目露出贪婪的精光。
长街上很快围满了人,那些指指点点似利剑一般穿过我的身体,少有的几句公道话也被诋毁声迅速盖过。
马夫拴住烈马,轻松将我抛上马背。
我忽然意识到,今日无论我跟马夫是否真的有染,众目睽睽之下,他都会在池琬的授意下坐实这件事。
博贤王府不会娶一个名声臭了的妻子,甚至整个池府都会因此蒙羞。
池琬是想让我死。
她一把扯出我口中的抹布。
“慢慢享受吧,阿姐。”
“我很期待,等裴小公爷看到你这副模样,会是什么表情。”
2
眼看马夫步步逼近,我拼命挣扎。
他所有裸露在外的皮肤都透着诡异的红,眼睛直勾勾盯着我。
此刻顾不上什么千金仪态,我双腿勾住马脖子,顺势滚落在地。
脚踝传来钻心的痛,可能是骨折了。
马夫觉得颇有趣味,摇晃着身子靠近。
“大小姐,今日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,你想去哪?”
我咬咬牙,前世那样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
今生更不可能折在这种龌龊的诡计下。
我滚得慌乱,小心在地下摸索刚才掉落的发簪。
握在手心的那一刻,便下定决心。
如到迫不得已,恐怕要自损以保全清白了。
一双玄色长靴忽地停在我面前。
正是谢家年初才被接回府的外室子。
谢临渊手中持着一卷书简,正垂眸看着我,喜怒难辨。
马夫被人打断好事,高声怒骂:
“哪冒出来的穷酸小白脸,竟敢坏我池府好事!”
眼看那只肮脏的手就要碰到我的手臂,我下意识抓紧谢临渊的衣角。
强忍泪水,“公子救我。”
我知道未来的时局变化,我有治世的才能,日后一定会尽全力报恩。
谢临渊定定看着我,一时间周围安静下来。
好看的眉眼微微蹙起,以书简为矛,逼向马夫的命门。
他没有说话,却从困顿中解救了我。
3
有人认出谢临渊的身份,马夫动作一顿,抻着嗓子给自己壮胆。
“就算你是谢家的人,也没道理干涉我们的家事。”
谢临渊单手解开大氅,将我从上到下裹住。
几声接连不断地闷响后,马夫的脸被按在马屁股上,接了满嘴新鲜热乎的。
谢临渊确认我无法行走,索性将我打横抱起。
我从没想过会跟他扯上关系。
一个是朝臣家不受宠的嫡女,另一个是世家养在外室的私生子。
或许是同命相连吧。
我红着脸圈住他的脖颈,整个人烫得快要熟了。
后知后觉自己刚才的举动,可能将他的处境也害得更加艰难。
他将我放进马车,亲自驱车到远郊的一处小院。
里面简洁干净,只有几个男仆和侍卫在。
他净手后,隔着丝帕握住我的脚踝。
“忍着些。”
眼前一道白光闪过,接骨的疼痛竟然比骨折更甚,我瞬间出了满背的冷汗。
抽着冷气问:“你怎么会这些……”
他为我倒茉莉花茶的手顿了顿,眸中的星光黯淡下来。
“你就当我是久病成医。”
我一时语塞,懊悔自己挑起恩人的伤心往事。
光是池府这种从四品官臣家里都满是龌龊,世家大族只怕更难。
我缓缓转动脚踝,躬身行了个周全的礼。
“谢公子大恩,池榆铭记在心,日后必有大恩回报。”
谢临渊看着我的脚,蓦地转了话音。
“你为何许久不来学堂?”
我猛然愣住,他怎么知道。
从一出生,我就注定是池家唯一的嫡女。
母亲身体孱弱,尚且在世之时,为我安排了两件事。
一是定下与博贤王府的亲事,保我一生无忧。
另一件是按照正室大娘子教养我,送我去学堂。
彼时我还小,池琬放风筝戏水的时候,我在念书。
她出去逛集会赏花,我在写字。
实在枯燥得烦了,我央求母亲也放我出去玩会。
下一秒,戒尺便落在背上。
“书中有宇宙间的锦绣山河,你尚未见过,便要被玩物磨掉心智。”
我忿忿反驳,“父亲说你这样毫无情致,刻板得很!”
母亲泪满于眶,手下打得更用力了。
“我要你念书不是为了哄夫君高兴!”
“入学堂,明事理,分奸佞。只要有一颗清醒智辩的头脑,再差的时局也不会拦了你前行的路。”
那以后,我没再发出过一丝怨言。
君子六艺,我要样样精通才行。
可未曾想十岁那年,母亲过世,蓉小娘以女儿家不宜抛头露面为由,大闹学堂,以至于我被所有民间诗会学府厌弃。
我日夜思念学堂,这点微薄心事也被知晓。
像是我独行在夜路上,在眼前忽然亮起的幽暗星火。
可我对谢临渊知之甚少。
前世我为了躲避闲言,跟马夫搬到遥远的水乡。
恍惚记得京城里有个冷面谢将军,杀人如麻,看样子总不像是眼前这位。
大约一盏茶的时间,我匆匆起身告别,家中这会怕是已经流言四起。
前有被马夫当街羞辱,后与外室子同乘一车。
哪样都不好解释。
谢临渊却拦在我身前,摊开手掌。
“你还没赔我的书。”
4
下人幸灾乐祸地垂头,用余光扫视我。
父亲阴沉着脸坐在主位,已经听池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谢临渊以索赔为名,实则又将我护送回来。
池琬的丫鬟故意大声尖叫。
“哎哟,这内室怎么进了外男,大小姐怕是已经暗中与人……”
父亲虽不喜欢我,但仍在意面子。
“闭嘴!”
“谢公子未递名帖便登门,实在不是世家做派。”
谢临渊也不恼,让开身子。
“事急从权,令爱的伤势不容拖延,您不检查一二?”
父亲闻言后才上下打量我,“府上有大夫,谢公子为何舍近求远?”
谢临渊仿佛听见什么笑话,缓缓勾起唇角。
“不若池少卿询问一二,这马夫所服的春药,是出自哪家?”
蓉姨娘登时变了脸色,急切地辩解着:“官人,重点是宁儿跟马夫之事,整条街上的人都看见了。”
“此时怕是已经传遍京城,真是家门不幸啊……”
池琬赶紧附和,“是啊父亲,在博贤王府聘书到达前,还是先行退婚保全脸面要紧!再行家法!”
我刚要跪下争辩,被谢临渊托住手臂。
“早听闻南郊池家是诗书人家,没想到妾室和庶女也如此受重,传出去才该颠覆全城百姓。”
父亲是言官,清名比性命还要紧,想到后果额间的汗已经顺着淌下。
“那今日之事也总该有个交代!”
谢临渊垂手立在一边,语气云淡风轻。
“马夫是家生奴才,生死都是主家一句话的事……”
池琬拼命阻拦,若人死了,此时没有人证,就变成下人欺压小姐,性质完全变了。
可能是谢临渊在身旁给了我底气,我不卑不亢道:
“还请父亲秉持公正,还女儿一个公道!”
大概是第一次被我忤逆,父亲一时间说不出话。
马夫被抬上来时,我才发现,方才在门外已经被谢临渊卸了手腕和脚腕。
药劲过了,脸上满上惊恐,不住地向蓉姨娘和池琬所在方位爬去。
谢临渊脚尖微微用力,便将人卷了回来。
“少卿大人的家事,在下不便插手。”
所以便插脚?
我怔愣地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耍诨,心中的郁结却在悄无声息地散去。
父亲闭了闭眼,大概是想尽快了结。
带着淬红的铁钉的板子只落下十几次,马夫就彻底没了气息,室内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
池琬和蓉姨娘勉强互相依靠,才不至于跌倒。
谢临渊恍若未见,淡淡道:
“主犯已伏法,该轮到主谋和帮凶了。”
5
今日之事必不能善了。
谢家官拜丞相,背后的势力盘踞在明暗的各个角落,如果谢临渊只是无人问津的外室子,倒也不算什么。
可偏偏他被接回,又入了宗庙,谁也摸不准谢家家主的意思。
父亲强压怒火,接过藤鞭,要蓉姨娘母女跪好。
又被谢临渊打断。
几次三番下来,父亲脸色难看至极,谢临渊忽而走上前,背对着我们跟父亲说了什么。
父亲的脸色立刻变了,声音都在发颤。
“那谢公子说应当如何?”
“自然是交由苦主决断。”
我么?
我按住心中的跃动,大方接过鞭子。
池琬吓得腿软,只剩一张嘴还硬着。
“你若敢打我,我必将百倍万倍奉还……”
好啊,如果她还有力气的话。
我想起母亲曾说过挽弓的姿势,劲巧而力大。
我高举纤细的鞭子。
而后,重重落下。
我数着每一鞭子,力求不遗漏。
第一鞭,为她不敬长姐,捆绑伤害。
第二鞭,为她陷害造谣,抹黑家门。
第三鞭,为她颠倒黑白,挑唆父亲。
第四鞭,第五鞭,第六鞭……
这些年来所受的委屈,每一件我竟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直打到池琬衣衫破碎,几乎衣不蔽体。
好在我还顾念外男在场,停了手。
父亲的脸色又黑又青,我猜是被这些闹人的哭声吵的。
可是还没完。
蓉姨娘像往常一样,叉着腰便要骂,被我一鞭子抽倒。
“我是嫡女,替母亲管教妾室,本就合情合理。”
蓉姨娘发现我动真格,半个身子躲到池琬后面,她先前被打得半死,根本没有力气逃跑,反而替蓉姨娘承受了大半。
好一副母女情深的模样。
我数够了三十下,恭恭敬敬地将鞭子呈给父亲。
他似乎累了,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知会。
我不敢回头看谢临渊,刚才我的举止未免像个悍妇。
谢临渊却步履轻快,对着父亲拱手:
“恭喜池大人府上恢复清净,在下也能说要紧事了。”
话音刚落,两队仆从鱼贯而入,将一担担的红色檀木箱子塞满了整个大厅。
“谢临渊今日求娶池榆,这是聘礼。”
6
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,只见一片坦荡的赤诚。
他给了我一个安心的眼神。
后面的事,未嫁女不能听,我被丫鬟带回房间休息。
不过短短两个时辰,发生的事竟如梦一样不可思议。
约两盏茶的功夫后,谢临渊找上我。
开口问我要书。
早些年,蓉姨娘因为妒恨母亲花大价钱为我求来满墙的古籍,趁我最后一次上学时,尽数烧毁了。
父亲也只是淡淡的让我搬到别院,并告诫我以后小心烛火。
所以递给谢临渊的,是我的手抄卷。
他没接,我垂下眼眸。
“多谢公子为我考虑,但也不必搭上前程姻缘。”
“明日我会主动向裴王府退亲,待风波过后,为保全彼此,还是少来往的好。”
这番话我踌躇了很久,想着怎样说才不显得自己忘恩负义,可又确确实实是为他着想。
他好像被我气笑了,凑近我的脸颊。
“叫我临渊。”
“除非我惹你生气,否则不要叫我的名字,更不要叫什么狗屁公子。”
我不明白。
“你是当真要娶我?”
从他的角度看,我只是一个空有嫡出名头的落魄女子,不受父亲宠爱,没有母家依靠。
就算马夫死了,还是会有各种流言,世家清流最怕内宅不宁。
我不是最好的人选,你要想清楚。
谢临渊无奈地夺过我手中的书。
“难不成我拿万金儿戏?”
“收了你的书,我也有一诺给你。”
“此后若你委屈,若不想跪,我便给你不必委屈的理由。”
他轻轻拉过我,落进他温暖的怀抱。
腰间有团冰冷坚硬的东西,瞬间让我呼吸一滞。